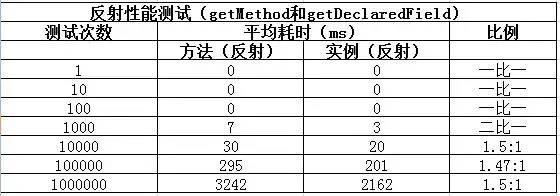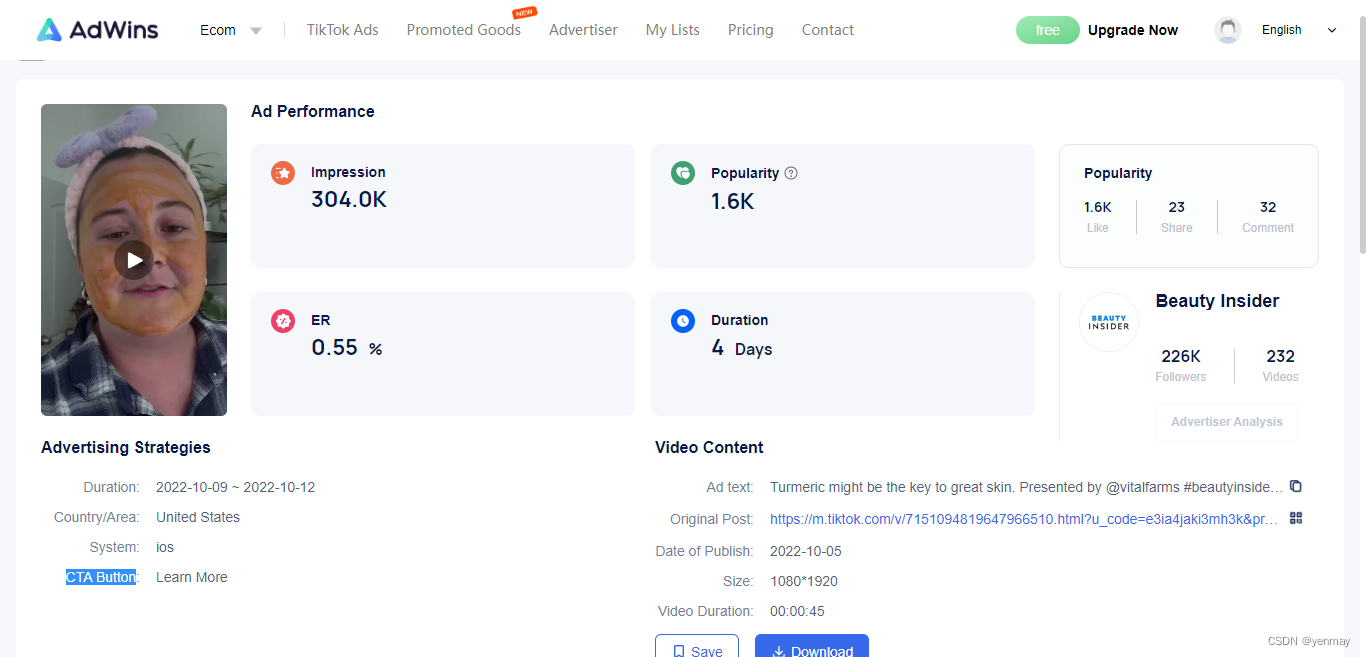尼日利亚拉各斯市,伊甘姆垃圾场。“生活按照重量衡量。”在这里任何东西都会用天平称量,报酬按照公斤支付。比如说,一麻袋电脑板和电线大约 11 公斤,价值 2 美元。
尼日利亚拉各斯市,伊甘姆垃圾场。“生活按照重量衡量。”在这里任何东西都会用天平称量,报酬按照公斤支付。比如说,一麻袋电脑板和电线大约 11 公斤,价值 2 美元。
 尼日利亚拉各斯市,Orile-Iganmu 的 Doyin 垃圾场。拾荒者从卡车上搬运电子垃圾并倾倒入垃圾场。这里的孩子们纷纷跑来并把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东西撕碎,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金属,尤其是铜和金。
尼日利亚拉各斯市,Orile-Iganmu 的 Doyin 垃圾场。拾荒者从卡车上搬运电子垃圾并倾倒入垃圾场。这里的孩子们纷纷跑来并把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东西撕碎,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金属,尤其是铜和金。
 尼日利亚拉各斯市,奥拉迪波(Oladipo)电脑市场。电脑市场中废弃的零件都被倾倒进运河中,在运河水位低的时候,拾荒者将垃圾从河中拖拽出来。由于这些都是有毒废弃物,使得运河边有许多燃烧着的火苗,回收充满危险。
尼日利亚拉各斯市,奥拉迪波(Oladipo)电脑市场。电脑市场中废弃的零件都被倾倒进运河中,在运河水位低的时候,拾荒者将垃圾从河中拖拽出来。由于这些都是有毒废弃物,使得运河边有许多燃烧着的火苗,回收充满危险。
 尼日利亚拉各斯市,Alabarago。Alabarago 目前在“钉子男孩”的控制之下(之所以这么称呼他们是因为,当你驾车穿过他们领地时,你一定会遇到困难,要么马路上会有撒满钉子的木板,要么在他们的手上会发现扎满钉子的木片)。他们用这些手段来劝过路人交纳保护费避免遭受人身伤害。如果你想来这里,你需要得到电子垃圾团伙头目给的许可证才行。
尼日利亚拉各斯市,Alabarago。Alabarago 目前在“钉子男孩”的控制之下(之所以这么称呼他们是因为,当你驾车穿过他们领地时,你一定会遇到困难,要么马路上会有撒满钉子的木板,要么在他们的手上会发现扎满钉子的木片)。他们用这些手段来劝过路人交纳保护费避免遭受人身伤害。如果你想来这里,你需要得到电子垃圾团伙头目给的许可证才行。
 尼日利亚拉各斯市,Ajegunle。Ajegunle 是一个收集并清理电子零件的垃圾场,也是拉各斯市许多有志于成为非音乐家的人的家园。男孩 Ashapo 在尝试从一堆将要被火烧到的电子垃圾中拿走一些电子器件时被烧伤了,他摔进了火中,颈部、脸部和胸部都被烧伤,甚至失去了一个脚趾。现在他靠买卖电子垃圾为生。
尼日利亚拉各斯市,Ajegunle。Ajegunle 是一个收集并清理电子零件的垃圾场,也是拉各斯市许多有志于成为非音乐家的人的家园。男孩 Ashapo 在尝试从一堆将要被火烧到的电子垃圾中拿走一些电子器件时被烧伤了,他摔进了火中,颈部、脸部和胸部都被烧伤,甚至失去了一个脚趾。现在他靠买卖电子垃圾为生。
 巴基斯坦,卡拉奇萨达尔地区。在电脑键盘和显示器外壳中使用到的一些化学制品和砒霜非常相似,能引发严重的皮肤问题和其他健康问题。
巴基斯坦,卡拉奇萨达尔地区。在电脑键盘和显示器外壳中使用到的一些化学制品和砒霜非常相似,能引发严重的皮肤问题和其他健康问题。
 巴基斯坦,卡拉奇尼亚里的 Surjani 镇行政区。Surjani 镇是一个主要垃圾场,大多数电子垃圾都被倾倒在那里,没用的废弃物会被倒入流向阿拉伯海的尼亚里河。这些污染物会破坏海洋生态环境。
巴基斯坦,卡拉奇尼亚里的 Surjani 镇行政区。Surjani 镇是一个主要垃圾场,大多数电子垃圾都被倾倒在那里,没用的废弃物会被倒入流向阿拉伯海的尼亚里河。这些污染物会破坏海洋生态环境。
 尼日利亚拉各斯市,伊甘姆垃圾场。“我们是穆斯林,我们都来自北方。对穆斯林劳动者来说,每天五次向安拉祷告非常重要。我们像家庭一样生活,我们是亲兄弟,因为我们说同样的语言,这种语言叫做‘豪萨语’,是北尼日利亚的主要语言。基督徒拥有一切,而我们只能靠他们的剩饭苟活。这是我们得到的全部。”
尼日利亚拉各斯市,伊甘姆垃圾场。“我们是穆斯林,我们都来自北方。对穆斯林劳动者来说,每天五次向安拉祷告非常重要。我们像家庭一样生活,我们是亲兄弟,因为我们说同样的语言,这种语言叫做‘豪萨语’,是北尼日利亚的主要语言。基督徒拥有一切,而我们只能靠他们的剩饭苟活。这是我们得到的全部。”

冰雪皑皑的格陵兰岛本该是一片纯净的世界,现在却被数不清的废弃电脑显示器和其他电子垃圾占据着。

尽管我们的文明在进步,但是我们对待地球家园和人类同伴的方式却越来越野蛮。
冰雪皑皑的格陵兰岛本该是一片纯净的世界,现在却被数不清的废弃电脑显示器和其他电子垃圾占据着。
这一幕让 Noor 图片社的摄影师斯坦利·格里尼大为震惊。“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重大选题。”
在斯坦利·格里尼看来,“追踪电子垃圾”这个纪实拍摄项目是为了“探寻那些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电子设备在寿命耗尽之后,如何因为政府与商人的刻意忽视,而对平民百姓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在三年多的采访报道中,他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研究调查方面。
斯坦利生于美国,师从著名人道主义纪实摄影家尤金·史密斯。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但斯坦利还是戴着车臣贝雷帽、太阳镜和大个儿银戒指,对生活充满热忱,对黑暗充满敌视,对普通人充满怜悯。
“尽管我们的文明在进步,但是我们对待地球家园和人类同伴的方式却越来越野蛮。”在这个追踪电子垃圾项目的前言中,他这样写道,“由于我们对地球和同类的漠视,我们正在污染自己的空气、土地、河流,甚至毒害我们人类自己。”
非洲大陆的电子垃圾进口之痛
“这里的人,生活是以重量来衡量的。这里的一切都是靠秤和砝码来计算,单位是千克和美元。
举例来说,一袋废弃电脑主板和电线,重 11 千克,你可以用它们在这里换走 2 美元。”斯坦利说。
据国际环保组织“巴塞尔行动网络”估计,每个月经过尼日利亚拉各斯港口的船运集装箱达 500 个,平均每个集装箱可装载 800 个电脑监控器或中央处理器,或 350 个大电视机。按照其容量计算,每月仅经过拉各斯港口进入非洲大陆的电子垃圾就相当于 10 万台电脑或中央处理器,或4.4万台电视机。
据报道,从美国到非洲装满废旧电器集装箱的船运平均价格是每个 40 英尺高的集装箱 5000 美元,而在尼日利亚市场上,一台能用的电脑的售价大约是 130 美元,一台 27 英寸电视机可卖到 50 美元。实际上,40台运行良好的电脑的销售额就可赚回一个集装箱货物的成本,因而即使集装箱中装载的大多数货物是没有用的废弃物,进口者们还是比较容易从这种危害环境的贸易中获利的。
据美国杂志《环境健康观察》刊登的题为《不公平贸易:销往非洲的电子垃圾》的文章报道,销往尼日利亚的废旧电器中,夹带着 25-75% 的电子洋垃圾。尼日利亚有一个兴旺的修理市场,却没有能力安全应对电子垃圾,大多数电子垃圾最终进入填埋场和垃圾场。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些电子垃圾可能带毒,其中许多装载着潜在的有毒金属,如铅、镉和汞。此外,电子组件通常有塑料包装,燃烧时会散发出致癌物质二恶英和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
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市最著名的垃圾场里,空地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电子垃圾、有毒化学物和生活垃圾。斯坦利发现,那些没有书读的穷孩子们竟然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天堂,他们在那里寻找可以再利用的东西,或者燃烧电子产品提纯需要的物质,却不考虑健康。原本应该待在学校的孩子们,在这里的身份是乞讨者和拾荒者。他们被那些成年人骗过来,替他们搜集电子垃圾,寻找那些可能含有铜或金的废弃电子原件,而成年拾荒者给这些孩子们的报酬却连应得的十分之一都没有,对待他们的态度就仿佛路边的野狗。
那些岁数并不大的成年拾荒者,自己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斯坦利经常看到他们三三两两赤身裸体地睡在废弃的泡沫板上,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和刺鼻的气味。“在这里,衣服和毯子并不是必需品。”斯坦利说,“最可怕的是感染伤寒和疟疾,因为没有药,这些病足以要了这些拾荒者的性命。”
站在这片垃圾场的高处拍照的时候,斯坦利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里的垃圾多得已经无法被彻底清除,政府也无能为力,将来也只会越积越多。我不禁扪心自问,这片规模巨大的电子垃圾坟墓,五百年后又将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在这里,你几乎凭肉眼就可以看见空气中漂浮的毒雾,如果将来在这附近修建居民楼和办公室,我相信没有谁能够生存下来。”
在拉各斯的另外一处垃圾场阿拉巴戈,黑帮“钉子男孩”控制着那里的一切。你不交过路费,那么你就要小心他们在你的必经之路上撒满钉子,或者直接用那些带钉子的木板敲碎你的头,这就是“钉子男孩”的来历。总之,如果你想进入这里,就一定要得到这群电子垃圾场黑帮老大们的特别许可。进出这里的一切,不论是人,还是垃圾,都得他们点头才行。相对于其他地区,这里的黑帮都是由穷人组成,实力相对孱弱,因为他们的收益大部分还来自于贩卖电子垃圾。
非洲渴望信息技术,但制造能力有限,这个大陆已经成为世界废旧电子设备处置的最新目的地。其中一些物资是由慈善捐赠者们提供的,多少具有一些功能,但经常有些安排出口事宜的掮客在装船运输时向集装箱里塞进无用的垃圾,这实际上使非洲的进口者们承受电子垃圾的重担。
来自外国的电子垃圾,在经过商人们的精挑细选之后,一部分可用的零部件流入拉各斯的奥拉迪颇市场,另外那部分毫无价值的电子原件则直接被扔进市场旁边的河道里。每当河水水位下降的时候,拾荒者们便会下去将他们认为可以收集贩卖的电子垃圾捡拾出来。在这条河道周围,到处弥漫着的刺鼻的气味和不时燃烧的火堆时刻提醒着进入这里的人,这里的环境是多么糟糕,甚至充满危险。每当雨季来临的时候,充斥着电子碎片的河水对住在河边的居民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特别是那些孩子。在拉各斯的马可可区,斯坦利观察到,很多建在水上的木屋干脆就是靠一些电子垃圾与木板混搭起来的。
一个生活在伊甘姆垃圾场的拾荒者对斯坦利说:“这里的人会像一个部落一样生活,因为我们都来自尼日利亚北部,讲同样的语言,信奉真主。我们辛苦劳作,靠双手拆解这些电子设备。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兄弟不小心被一台计算机或者别的什么机器里流出的不知名液体迸溅到了他的嘴里和胳膊上。这有毒的液体不仅仅烧伤了他的皮肤,最终还要了他的命。可我们唯一能为这位部落兄弟做的,就是埋了他,然后忘掉他。”
为了生存,放弃未来
“在工作现场,虽然空气中充满高浓度的化学物质,但是工人们没有丝毫的防护措施。他们认为,只要多吃一些黄油等食用油,就可以抵御这些化学物质对身体的损害。”在印度,分解电子垃圾的工人这样对斯坦利解释自己为何不惧怕这些隐形的健康杀手。
这里的人对于电子垃圾危害的认识让斯坦利深感荒诞。
在完成了对尼日利亚电子垃圾场的采访后,斯坦利动身向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进发。为了这次拍摄,他已经准备了两年半,按照自己的计划,他将会在尼日利亚、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各待一个月,去探访那些早已经熟知的电子坟场。
在印度,他看到那些回收厂的工人们为了得到每天四美元的工钱,一刻不停地在垃圾堆里拆解电脑主板、变频器以及其他电子废弃设备。回收商销售从电子设备中清除出的金属而从中获利,但是找出有用的金属的工艺过程是非常有害的。工人经常是在没有保护设施的情况下做清除金属的工作,吸进高度有毒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又被排放到空气中。这些过程大多发生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这些国家没有法规保护工人或者阻止原始落后的回收利用工作。
尽管已经回到远在另外一块大陆的家里,但是在亚洲的所见所闻,仍然时刻出现在斯坦利的脑海中。“世界上只有在这里,任何一天,你可以看到上千的妇女坐在那里,在煮电路板。他们正在吸着溴化的阻燃剂和正在被加热的铅和锡。你可以在空气中闻到味道。一进入这个地区你就会感到头痛。实在是很糟糕。”
焚化电子产品会释放大量重金属如铅、镉、水银充斥于空气及灰烬中。水银释放在空气中会在生物链中累积,尤其是鱼类,这是传入人体内的最主要途径。如果电子垃圾含有 PVC 塑胶,二噁英和呋喃也会因而释放。在燃烧电子垃圾时,溴化阻燃剂会产生溴化二噁英和呋喃。
尽管危害巨大,但是由于电子设备回收利用是一项非常有利可图的生意,仍然有许多人铤而走险。
在一些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回收商可以仅仅是名义上的,这些所谓的回收商发现,他们仅仅出口这些材料就能赚很多钱,因为美国法律完全允许这样做。他们可以用不违反环保法律的方式做这些事,又将实际的成本输出。据一家环保机构介绍,每一天都有成百的集装箱装满电子垃圾离开北美,向亚洲或者非洲驶去。
“面对生存还是未来,许多人会毫不犹豫地放弃未来。”斯坦利说。
在印度,焚烧电子垃圾是违法的。可斯坦利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金奈采访时却发现,每到深夜,还是有很多人偷偷摸摸在垃圾场点火焚烧垃圾。虽然曾经发生过几次回收工人中毒事件,但是金奈的电子垃圾回收产业仍然欣欣向荣。一位工人向斯坦利抱怨说,自己如果不被毒死,那一定就会被累死。
在礼拜天的市集上,你只要花最多 80 到 100 卢比,就可以雇一个挑夫把电子垃圾拉到郊外荒地上,卖给那些收电子垃圾的小贩。在最近的四到五年中,金奈的电子垃圾回收市场发展非常迅速。斯坦利说,这原因非常简单,原本在欧洲国家需要上百万才能做到的电子垃圾回收工程,在这里,你可能只需要几百欧元就能办到。因为这里有世界上最低廉的劳动力和几乎不存在的健康保障。斯坦利再一次对西方文明产生了质疑,“难道我们这个自以为是的文明社会,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制造垃圾的社会?而且是越文明,制造的垃圾就越多,甚至现在开始抛弃我们自己的人类同胞。”
消费主义的代价
自 1989 年《旨在遏止越境转移危险废料的巴塞尔公约》签署以来,联合国 145 个成员国以及欧盟一直在寻找彻底消除这些危险的垃圾的方式。但是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大,一些缺乏有效管理机制的发展中国家成了垃圾回收商们出口电子垃圾的目标。那些电子垃圾身上残留的价值,让这些贫穷的百姓急切而不考虑后果地投入到这场废物回收浪潮之中。由于电子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随之而来的电子垃圾也越来越多。
斯坦利说:“在西方,回收一台旧电脑需要 25 美元,可在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可能只需要 1 美元,甚至更少。虽然 90% 被运往这些国家的电子产品都是可以被修复再利用的,但是显然,直接扔掉它们远比修好它们所带来的利润更多。在我们这个数码时代,新的才是好的。”
与中国不同,在印度,工人们很少考虑循环利用这些电子垃圾。他们的做法更加简单直接。在新德里东部的小镇,工人们通过分解电视机、电脑显示屏、电路板、变压器以及手机,来获取黄铜、金等等贵重金属。而这些回收厂就藏在一户户的村民家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和小孩子一起从事这些危险的工作。
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斯坦利遇到的电子垃圾收集者是一群来自阿富汗的孤儿。这群孤儿被雇佣去在旧电脑中分解出铅、铜,同时还要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焚毁那些没用的却有毒的电子原件。平时,这一群二十多个来自坎大哈的孤儿就睡在一间狭小的临时棚户内,他们靠四处寻找被丢弃的电子垃圾为生。为此,他们每天都要走遍卡拉奇市区内大小 300 多个垃圾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长期缺少营养,瘦骨嶙峋。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必要的电子设备太多了。”斯坦利说。9月 24 日晚,苹果宣布 iPhone5 在上市后前三天的销量就超出了 500 万部,可以想象,当这 500 万部手机被送到消费者手中的时候,究竟又有多少部旧手机被当作货物出口到那些发展中国家,给当地制造出多么可怕而肮脏的难题?
在中国拍摄时,斯坦利遇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家所在的镇子非常贫穷,绝大部分人都靠收集电子垃圾为生,但有些人家通过收集这些电子垃圾变得非常富有,比如这个女孩家。富起来的人家也和这个女孩子一样,开始追逐最新的电子产品。“她手里拿着的是一部 iPhone5,在中国还没有正式上市。你知道么,我当时感觉特别荒谬,我那一整天拍的都是被粉碎的 iPhone4。”
对于今天的世界,斯坦利非常愤怒,“当第一盏电灯被爱迪生发明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帮助我们获得更加安全的光明,如今它仍在工作。可是今天呢,我们所制造的一切并不是为了能够持久地使用。比如我这台电脑,用了四年就出现问题。现在的人类社会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一个制造垃圾的商品社会,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将人类自己也像垃圾一样抛弃。”
站在电子坟墓上,斯坦利久久无声,注视着那一片片剧毒的烟雾飘向自己,飘向远处。
B=《外滩画报》
SG=斯坦利·格里尼
“我们的文明让我们成了这些短命商品的奴隶”
B:是什么促使你在 2009 年后开始进行这个横跨大洲的拍摄项目?
SG:起初,我和 Noor 的摄影师们一起关注全球气候变化这个选题。我的任务是去拍摄北极圈里面的爱斯基摩猎人,关注气候变暖对他们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他们生活的境况让我震惊,不仅仅是冰雪消融让猎人们一无所获,更在于他们和北极动物的家园正在被一艘艘货船向这里倾泻的电子垃圾侵蚀。于是,我试图寻找这一切发生的根源,为什么人们要在这里倾倒电子垃圾。为此我做了很多研究工作,随着调查的深入,我越发觉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开始,我原本计划去拍摄五个国家的电子垃圾问题,包括加纳、尼日利亚、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它们的问题最严重。但是后来我看到很多摄影师已经去加纳拍摄过,我不想重复,所以最终选择了另外四个国家作为我这个追踪电子垃圾项目的拍摄目的地。
B: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什么?
SG:作为一名摄影师,我想了解在这些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地的人们为什么要去接收这些来自西方的电子废物,是什么样的利益驱使人类建立这样的电子坟墓。但是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当地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一个严峻问题。即使是现在,当我把照片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不明白你拍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因为这些电子垃圾,一些人的健康正在恶化,正在死去,失去生存的权利。而另外一些人,则把这些毒物看作是一种有趣的玩具,比如越来越高科技化的电脑、手机。在很多地方,人们努力工作,拼命赚钱,就是为了拥有更新的玩具,然后把那些旧的扔掉,送往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的文明让我们成了这些短命商品的奴隶,然后成为被自己生产的垃圾剥削、损害的生物。我不可能阻止这一切,但我试图用照片延缓这种速度,这种发展的速度。
B:在拍摄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SG:虽然我做了很多调查和研究,但是当我真正踏上这片电子垃圾场的时候,我还是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这里就像一座巨大的黑色坟墓,里面充斥着来自西方文明的电子残骸。生活在坟墓里的人们,把这里当作了自己淘金的乐土。
B:在采访中,你同样受到电子垃圾的毒害,难道你不害怕么?
SG:我喜欢挑战那些有难度的报道选题。在格陵兰的时候,同事们说我应该好好感受一下那里的冰川美景,这或许能够让我从那些恐怖的战地报道中解脱。但是,当我站在冰川上,我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电子垃圾。后来我发现,是一艘艘的货轮将这些垃圾运到了这里。
这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我的实习生、助理和我一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调查。我们发现,尼日利亚、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是电子垃圾的最主要去处。后来我们发现,这些可怕的电子垃圾,那些曾经代表着时代最进步科技的东西,正在危害当地人的健康,甚至置人于死地。这太恐怖了。再后来我们还发现,这些电子垃圾同样带来诸如童工问题、奴隶问题等等反人道的犯罪。我的脑海中一直有这样一幅场景,一个宽敞的屋子,堆满废弃电脑主板,一位瘦弱的老女人在熔炼它们,可她暴露在外的双手已经由于长时间被化学毒素侵蚀而开始腐烂。
“我的责任就是一名信使”
B:你觉得自己的作品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变化?
SG:在我采访的一个小镇,整个镇子居民的收入都来源自这些电子垃圾,所以这是不可逆转的。我的一些朋友,拥有五个手机也属正常,所以我无力改变,只能尽可能地去让它变缓。另外,你可以在那张巴基斯坦拍摄的照片里看到一些政府或大公司的警示画,在警告人们从事电子垃圾回收是对个人身体有极强危害的。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作品,警醒越来越多的人,在不得不从事这项危险的工作的时候,注意对身体的保护。
我希望那些生活富足的人们可以通过我的照片,了解到他们随手丢弃、更换的旧机,对其他人或许意味着很多。作为一整个电子产业链中的一环,你们必须关心生存于同一循环中的其他人。我们是人类,有人性,所以必须小心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会伤害他人。我并不是说,我们以后不要用手机、不要用电脑,而是说,制造者应该生产更加耐用的产品服务社会,而消费者应该把这些电子产品当作工具而不是玩具,不喜欢了就当作垃圾丢弃。
B:拍摄的困难是什么?如何找到合适的“向导”?
SG:这个拍摄需要充分的前期调查。光靠我一个人是无法独立完成的,所以我会向朋友、同事询问,谁认识那样的人,可以帮助你进入拍摄地。有时候,你就径直走向离你最近的那辆出租车停靠点,也许那个司机就能够成为你的好向导。或者去大学,也许一些希望通过兼职来赚些钱的大学生能够带给你意外之喜。有时候,一些陌生人会主动给我写信,希望能够参与到我的工作中来。在尼日利亚的时候,我的线人告诉我,那里的垃圾场都是黑帮控制的,很危险。可实际上,那里的黑帮也都是一些一无所有的穷人组成的,他们对我漠不关心,只关心自己的“收成”。
B:一些照片中人的表情往往带着一丝愤怒和忧心?他们是否把自己看作电子垃圾的受害者?
SG:不,他们仅仅把这看作一项可以让自己吃饱肚子的工作。让他们不开心的原因,可能是迟迟没有发的工钱,而不是对身体健康的担心。而这样的人更值得我们同情。在尼日利亚阿杰甘勒垃圾场,废弃的电子产品被有序地归类和清洁。一大群怀揣音乐梦想的年轻人长期居住于此。其中一个男孩打扮得好像迈克尔·杰克逊,面对镜头他跳起了太空舞。可是他告诉我,自己曾经在一次提炼电路板中的金属时,不小心引起了大火,烈火给他的脖子和胸口留下了伤疤,同时带走了他的脚趾。可是如今他仍然一边买卖电子垃圾,一边模仿当红歌星唱歌跳舞。
B:在回到工作室后,你对那些胶片作品是否满意?
SG:我希望能有机会去拍摄那些电子产品,比如电脑、手机是如何被生产出来,即记录它们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但是很遗憾,那些大公司不允许,另外我的资金也不够支持我独立完成这样一个庞大的报道项目。为了目前的拍摄,我花费了 37000 欧元。
B:纪实摄影师的责任?你的摄影哲学是什么?
SG:我的责任就是一名信使,我把发生的事实用照片讲述给大众,让人们知道在那些公司精美广告和政府宣传的背后是什么。我的摄影哲学非常简单,就是去现场,把黑白是非呈现出来,寻找黑暗中人性的光芒,或者在光下寻找人性的黑暗。所以我常常去做的事情,就是到一个地方,去观察那里的人的行为,去寻找他们这种行为背后的动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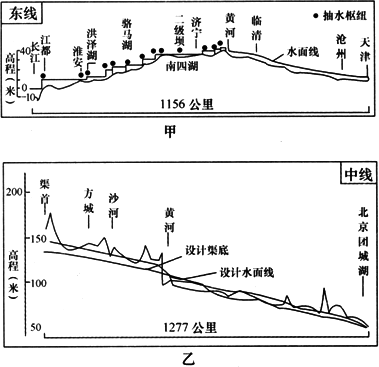





![[论文总结] 深度学习在农业领域应用论文笔记2](https://img-blog.csdnimg.cn/20200924221714364.jpg?x-oss-process=image/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NzcxNTQ4Ng==,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