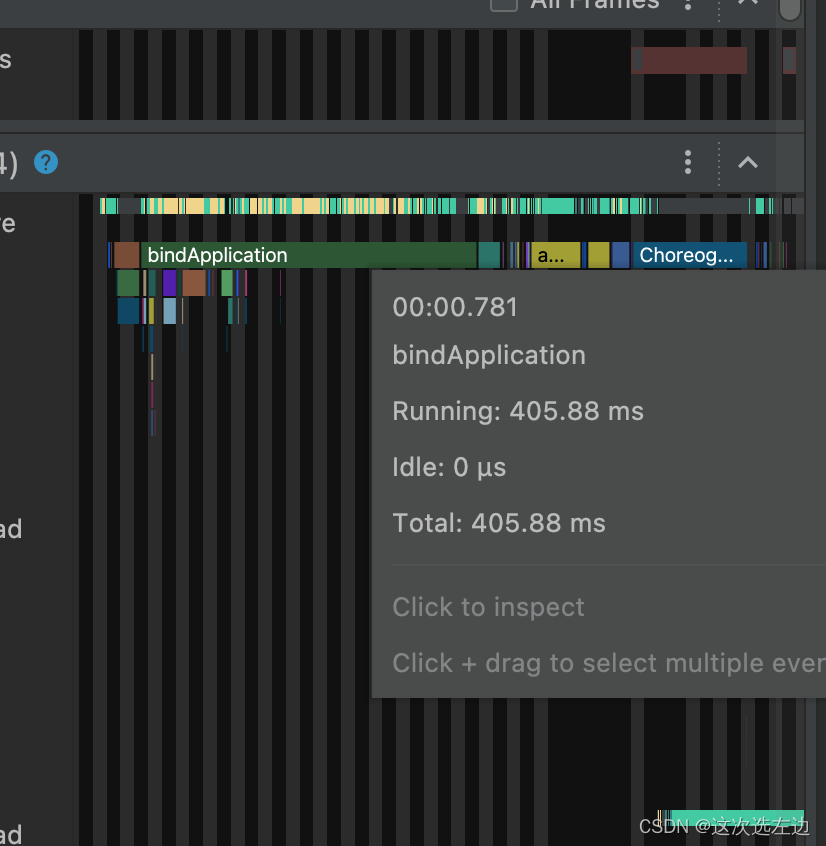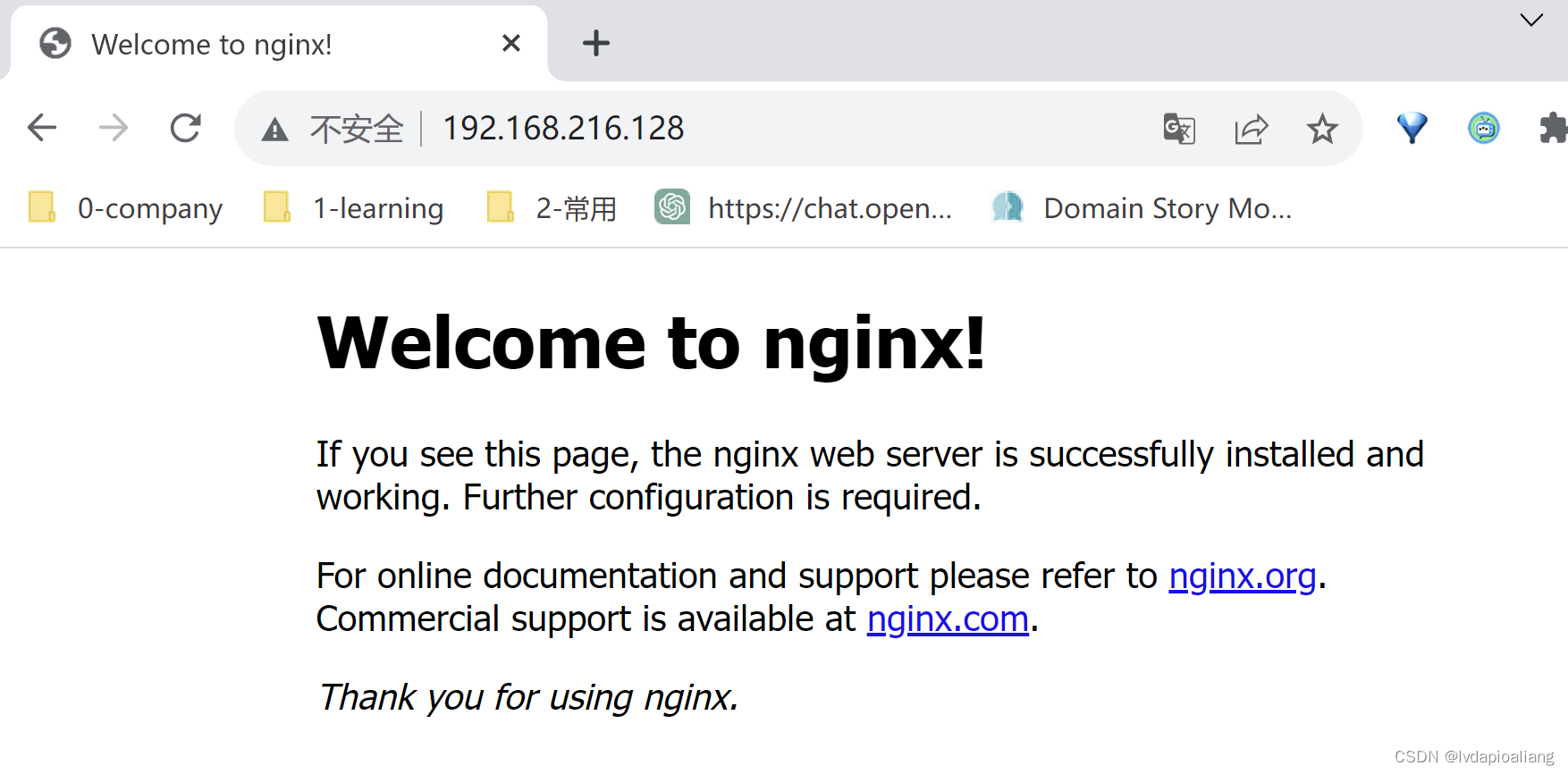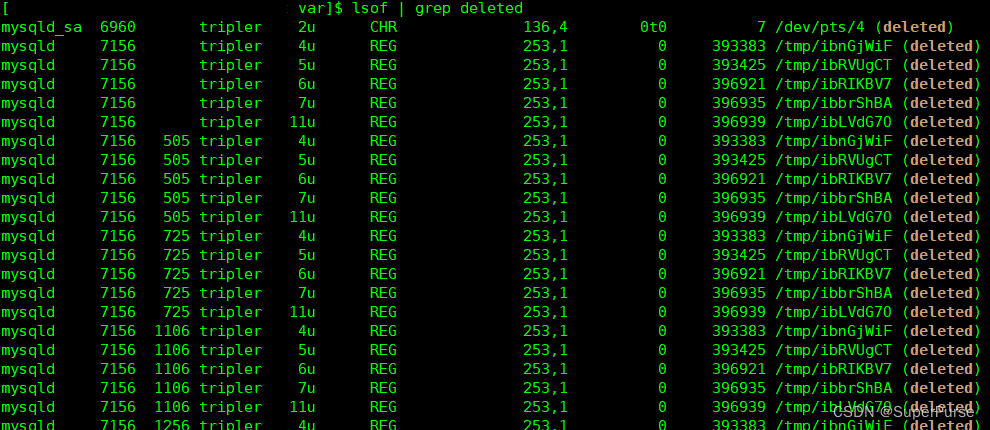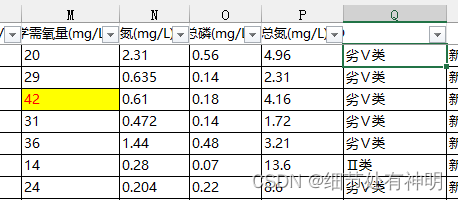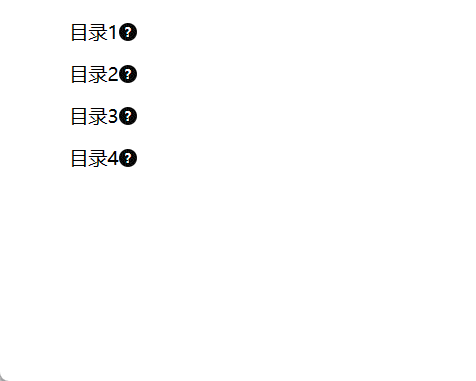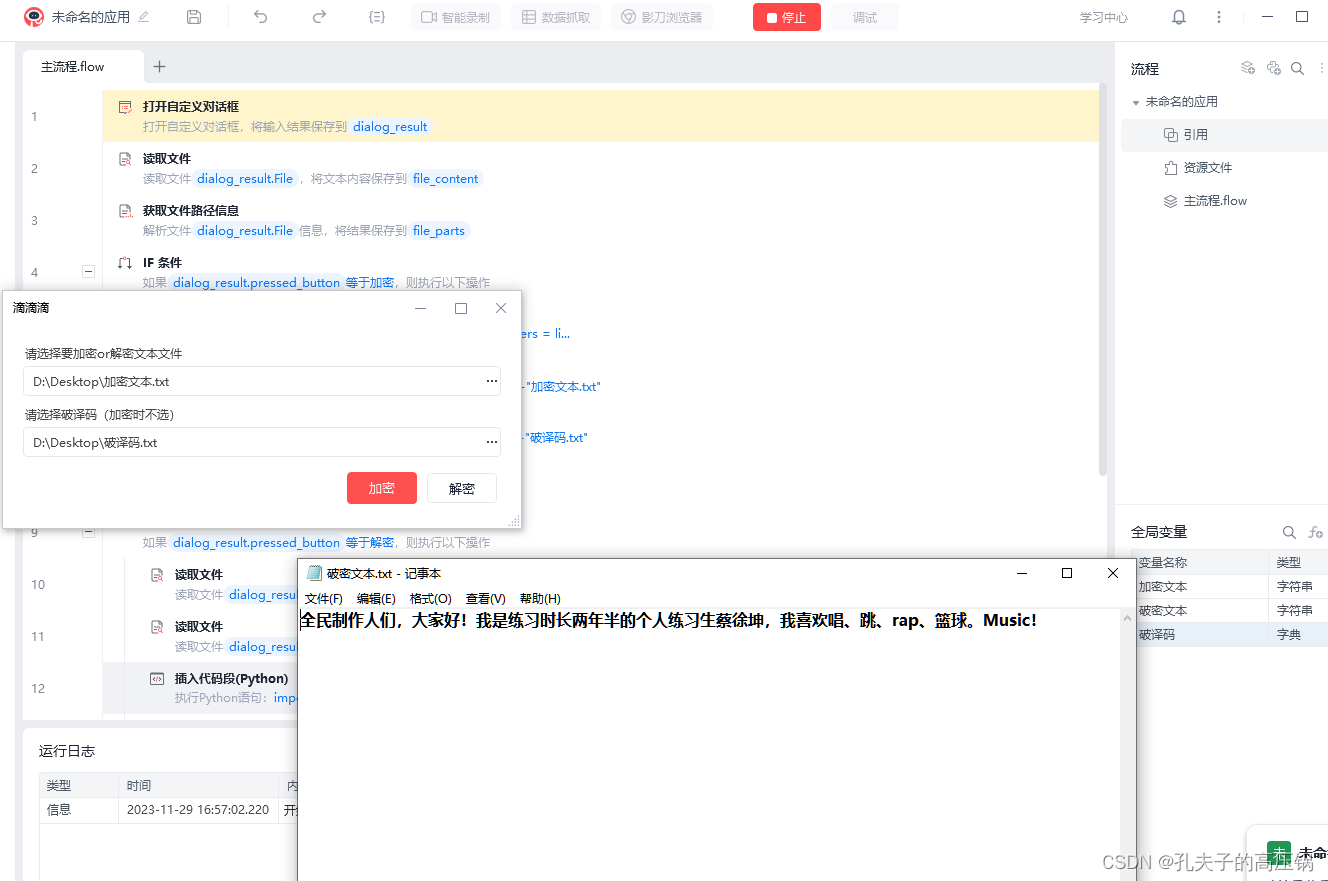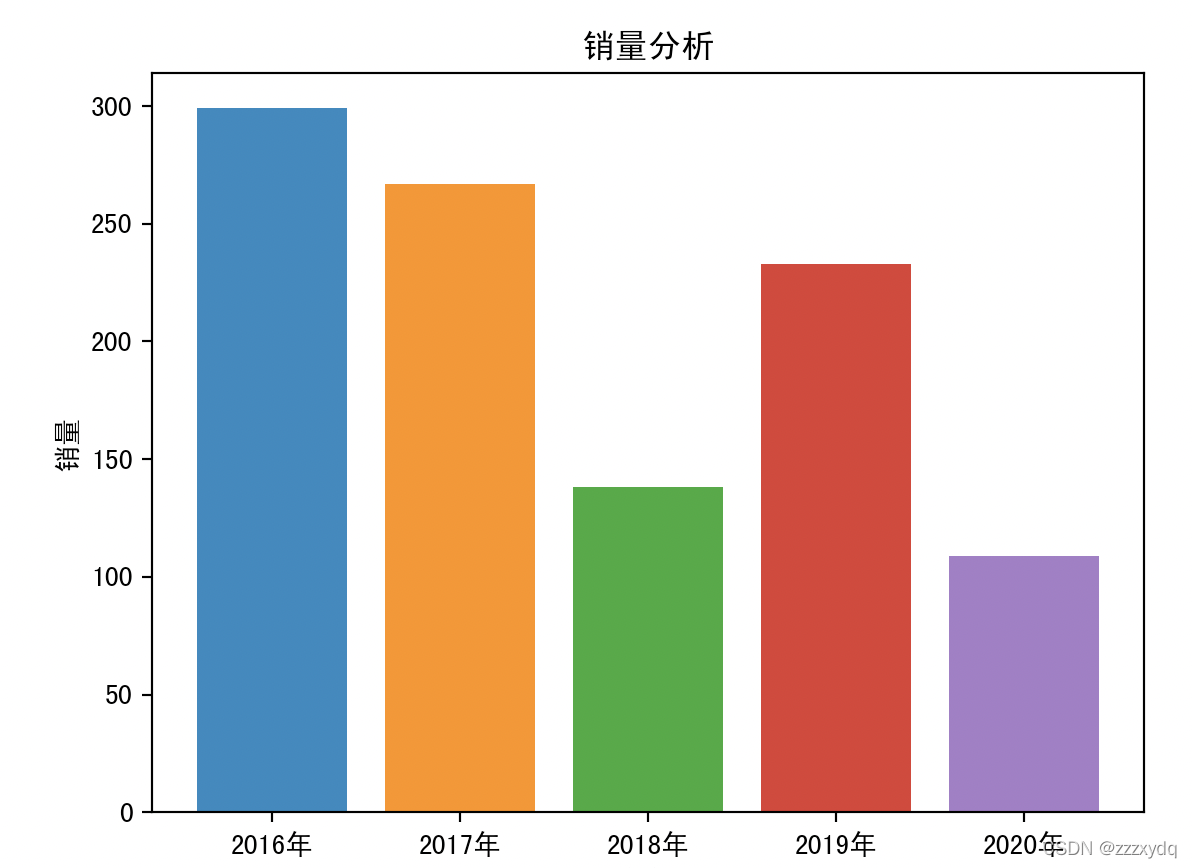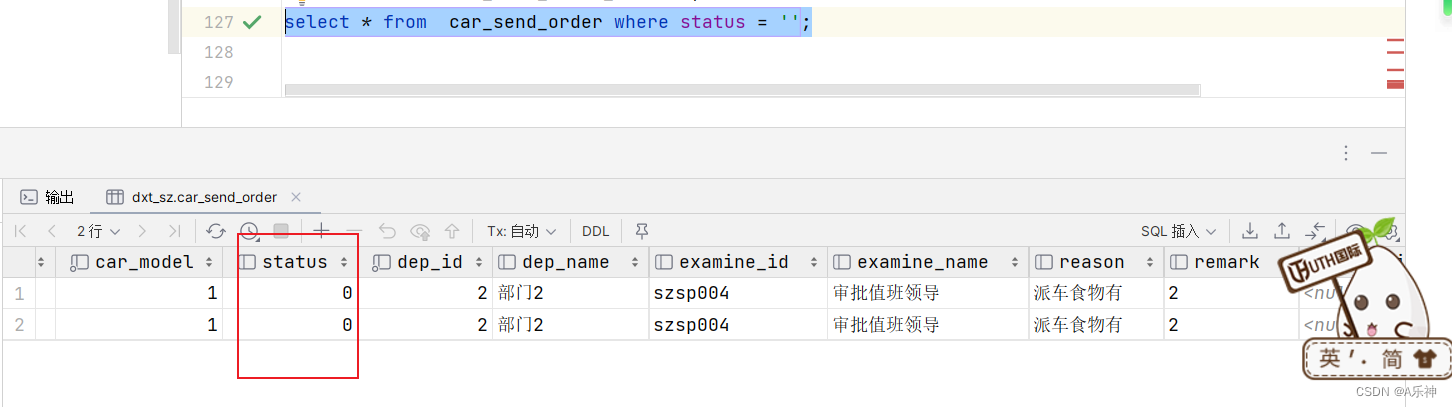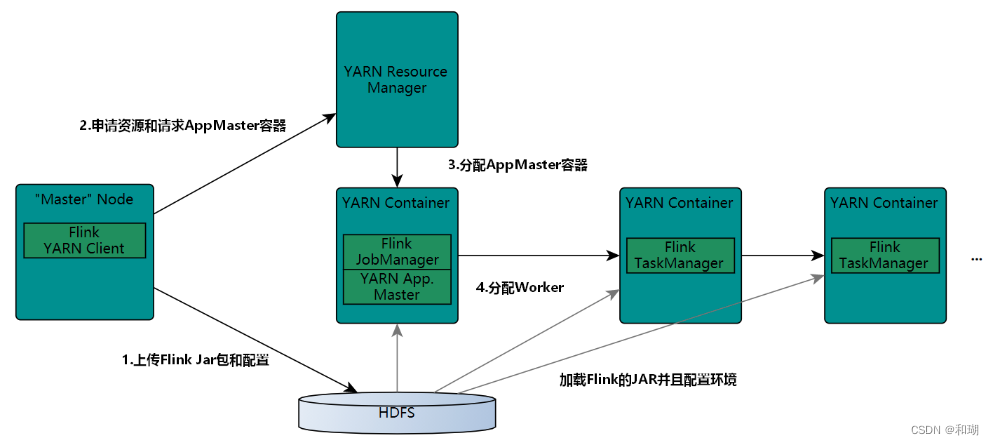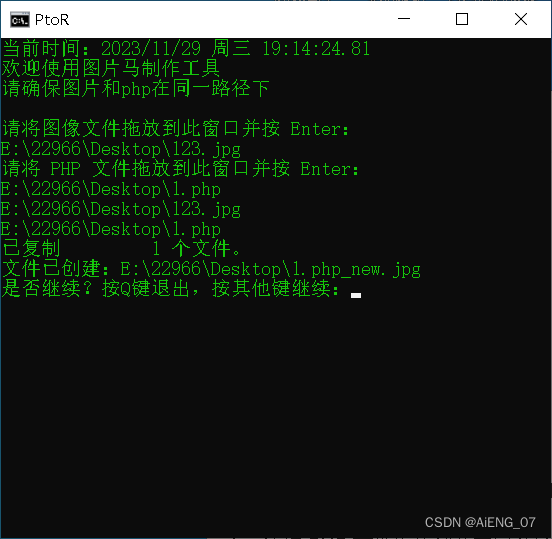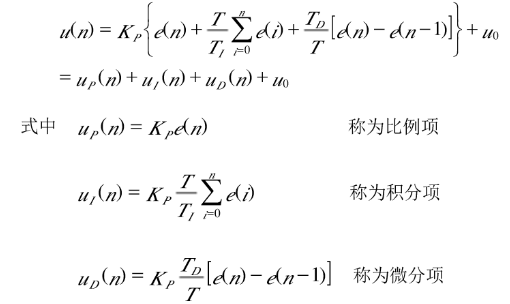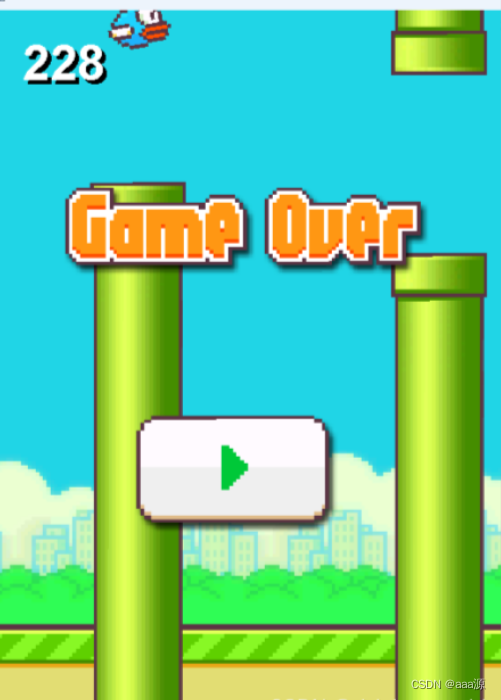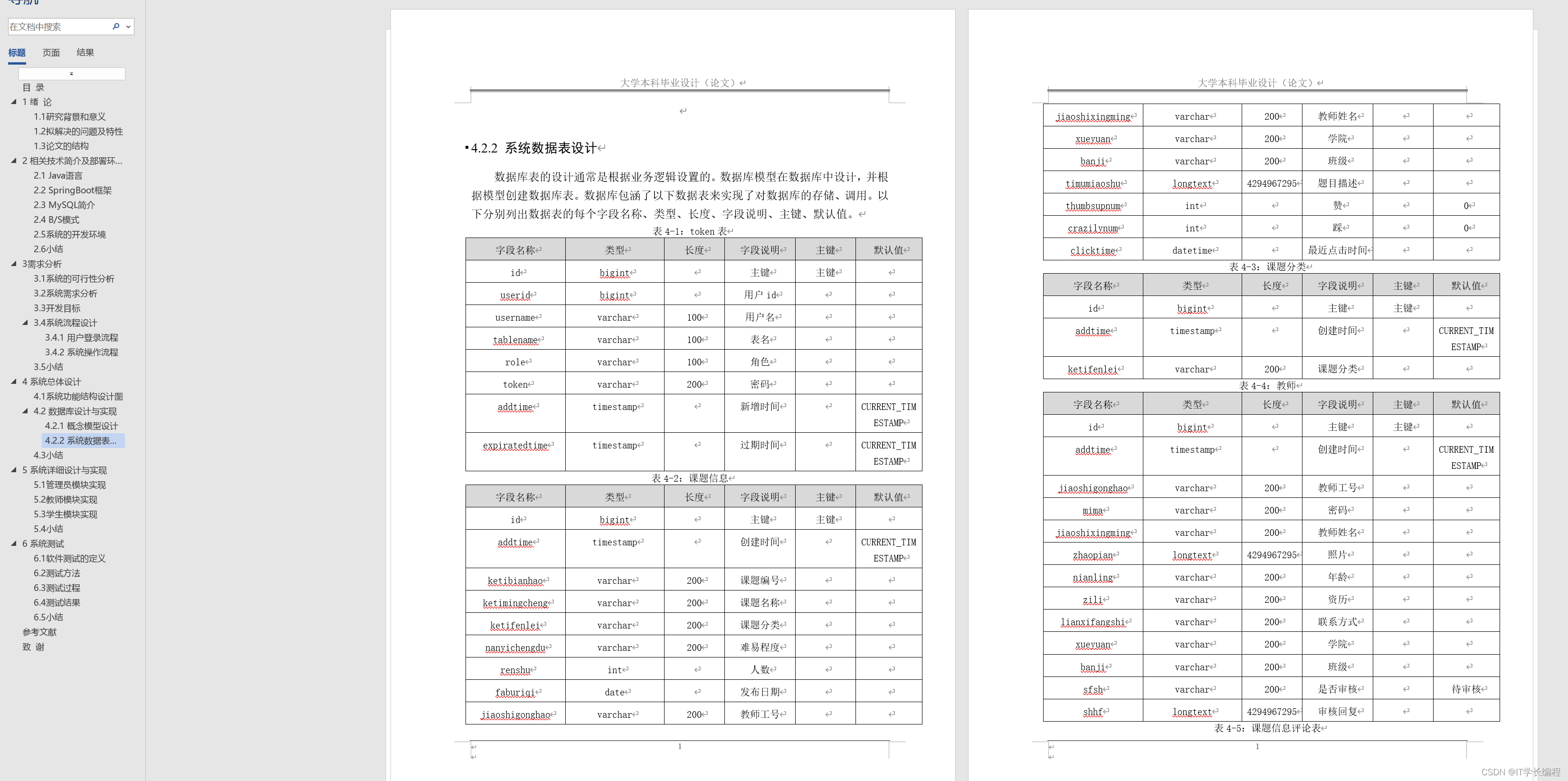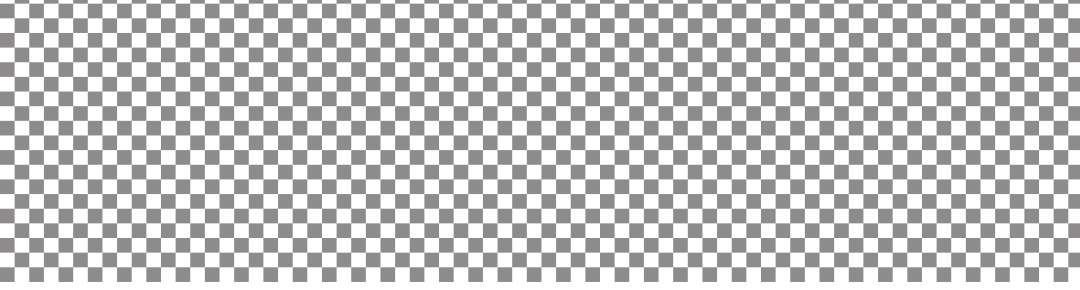回忆何家桥往事,写了篇《消失的何家桥》,没想到点击率如此高,出乎意料。网友的共鸣可见,城市发展的今天,乡情是个美好的存在,清贫、朴实,丝毫不影响美感。由于大家的鼓励,触动了我再想写点乡情的冲动。其实,在我上学年代,文史哲三科成绩,史哲尚好,而文学最次。哲学出于家传,历史发自爱好,唯对文学一直不上心,没有进步。岁数上去了,写作有益健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选择,应当坚持。这里所写何家桥往事,仅限于上世纪七十代的事,因为六十年代我尚无记忆,八十年代已离开老家。

说起我老家边上的这条河流,不得不提到家门口的这个石板水桥,这是五块大石板上下叠成,有四阶,它是平时周围村民生活所依赖的地方,如淘米、洗衣服、挑水等。因为河流是活水,是流动的,所以没什么污染,但也谈不上算清澈。我有时站在水桥上四周眺望,常会在无意间凝视到河水,突然觉得站着的石板猛然变成了恒速移动的小船,这种错觉就是由于水流引起的。
这条河的上游通向蕰藻浜直至长江分支,所以从老家向北望去,经常会看到一排排帆船移动着远去。下游是通向南陈家宅及附近小村。每年台风季节往往会大水猛涨,水桥经常被淹没。
有一次见河水淹了两级石板,我依次而下,由于判断失误而不小心踩空,整个身子坠落下去,还好本能的一阵乱蹬才始脑袋露出水面,自己爬上了岸,看看四周沉寂,不见一人,顿感后怕,自认命大。
这条河冬天一般会结薄冰,在结冰到够厚时可以走到对岸,但这种机会并不多见。

河里有着丰富的鱼虾蟹之类水产,垂钓、摸蟹是男孩子喜欢做的事。村干部每到过年前都会组织大家把河的两头狭小处堵上,再用抽水机抽干河水,然后由专人捕捞鱼虾,统一送到村广场进行按家按户分配,算是发个“海鲜年货”。
因为当年是人民公社,何家桥编制是生产队,村里的一切都姓“公”,属于集体所有。如有一次村里死了一头耕牛,闹得动静很大,像是村里发生重大事件一般。然后杀牛现场我也去看了,有个村民要求留个牛角给他,说刻章用,印象很深,至少我长了见识。事后家家户户都分到点牛肉的,在家门外都挂着晒干,做成牛肉干。

我们何家桥还有个大“企业”,就是在村广场边盖起的三四间蘑菇房,里面隔起多层蘑菇种植地,也是我们小孩在里面玩躲猫猫的好去处。蘑菇长成后,要切下标准的统一外销,切下的残留蘑菇根是留着分给村民的福利。那时因为吃不到完整蘑菇,就以为一定比蘑菇根好吃,后来有条件吃上了才知没什么特别感觉,甚至觉得蘑菇根更香。
何家桥除了石板桥外,村里的那棵大树我觉得应该算得上是标志性东西,虽够不上高级别的参天大树,但是它见证何家桥的历史足够有余。夏天村民常聚集在树下纳凉、聊天。

记忆中我家有只老黑猫,吴家有条大黑狗,在村里是比较显眼的,可能是因为它们属于老资格级别的。有一次休闲中的村民在这棵大树下见到这对黑猫、黑狗偶遇,就不嫌事大,起哄着来个狗猫大战。我家的黑猫见势不妙迅速地窜上大树,黑狗在人的鼓动下表现出非常积极,就坐在树下抬头仰望,随时准备战斗,我是真的担心我家黑猫会吃亏。时间过了很久,黑猫没有耐心了,趁黑狗不备突然窜下树飞一般地逃走,黑狗紧追不舍但终究还是没追上,由此感觉我家黑猫是胜利者。
我们是借住于外公家的,小时候也跟着表弟、表妹喊爷爷。外公考虑到小舅舅也已长大成人,就计划让我家另建新房搬出来。后来经过多方磨合,上级村委批准在前面大树旁的空地上建造,并指令锯掉大树,这实在可惜。

父亲在大学工作,有固定工资,但为了凑够钱,还是卖掉了不少民国版藏书。后来好不容易购买到的一船红砖总算通过水运到达河岸,家人立刻组织了村友们马不停蹄地搬运到宅基地,并很快开始动工打地基。我是看着房子一点点造起来的,那年我也就六七岁的样子,还没正式上学。
当时没有专门的建筑队,都是就近村民中按特长临时组建的业余建筑队伍,并按习俗规矩,本村每户人家都要出劳动力来协助、帮忙。最后是上梁环节,我见工人在横梁上行走自如,非常好奇,至今难忘。
据说我家新房地基打得不深,经不住大水浸泡。有一年,记忆中最大的雨水天,全村都被水淹掉了,吴家地势偏低,家里的水已淹到膝盖处,我还和小伙伴们趟着水过去现场体验了一把。当时村里标志性的石板桥也被淹没了,村长是躺水到那里用竹竿插在桥边做记号的,防止人们不小心掉到河里。好在大水很快退去,不必再为房子会不会塌陷而担忧了。

村外还有个圆形筒桥,是水泥筒一节一节拼接起来的,实际上是引水渠之水到对岸的管道,不过在农村多个过河的桥会省去很多绕路的时间。
这个“圆桥”平时很少有人过,但却是小孩子们的玩耍去处,我是到大点才敢走过去的,还是要有点平衡能力和勇气的。听外公说这座桥是两个舅舅小时候经常逃学的地方,因为桥在村外不容易被人发现。
老实巴交的外公也有他惊人的一面, 据说早年的深夜有强盗来抢孙家,外公被惊醒后从后院跳河躺水到对岸去邻村的北陈家宅呼“救兵”,然后他们“敲锣打鼓”地造势来吓退强盗。

陈家边上有片竹林,空地是夏天避暑纳凉的休闲处,村民在那里侃侃而谈,犹如“竹林七贤”。竹林里有个没有挖深的大坑,一开始见大人们不知挖什么,后来才知是中苏紧张,挖防空洞作隐蔽之用,配合“备战备荒”的宣传,后来因为土质太松而塌陷,说明当地根本不具备挖地道的条件。
当时也经常看到民兵训练、开会,他们提的都是真枪实弹。我一个年长的表哥分到的是挺轻机枪,拿回来放在屋外头,引来了好多小伙伴们的好奇之心,大家都只有从电影里看过,于是大家都轮流着把玩过瘾。挨到我时,因为年龄小,只觉得枪身很沉重,提起来走路很吃力,但由于一直有英雄情结,所以练起枪来很投入,乐此不疲。

由于何家桥属于微型小村,在合作社时,就与隔壁的北陈家宅大村合并成一村,村长轮流做,但许多的大型活动还都以北陈为主,以至后来村里有了实力买黑白电视机时也是由北陈来管理,害得我们何家桥这边的人去看个电视要走好多路。当然,相比之下,在没买之前去南陈家宅蹭电视看要走更远的路,且还要受冷眼相向自然要好得多。
北陈村口有一棵标志性的大树,树上挂着一口大钟,也忘了是铜的还是铁的,钟下吊着根粗长绳,在出工、下工、开会或紧急集合的时候都会有专人拿绳敲得当当响,不用时就把绳子绕树打个结挂着。这口大钟算是两个村合并后共享的一个重要作息装备,这个情景不由得让人想起有点像电影《地道战》里的镜头。

小孩天性好动,一旦得到村干部宣布当晚要全村开夜工消息,就是大人们要干通宵达旦,挑灯夜战,这也一定会乐坏我们的小伙伴,开始幻想着晚上可以如何疯狂地玩闹,同时也羡慕或十分佩服那些消息灵通、最早获知信息的小伙伴。
为了晚上夜工,白天要早早地在工作场地周围忙活着搬动机器、马达等工具,还要按装、悬挂好太阳灯,要做好一切充分的准备。晚上有打麦子的,有挑麦秆的,有打扫的,大人们都忙得不亦乐乎。很快麦干堆积如山,小孩子由此“登山”,爬上爬下,兴奋不已。
村里架电缆较晚,所以晚上都用油灯。后来总算全村通电了,接着每家每户按装广播喇叭,但那时不是整天有播放的,从早晨到晚上分时间段地播放歌曲、电影、戏曲等,重复多。记得每当听到播放《东方红》歌曲就说明中午时间到了,这在当时还没有钟表普及的情况下,喇叭里的固定节目大致可以告知你一天的时间段。

农村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开挖河流工程,集中当地各村的强劳动力,统一行动,大力开挖运河工程。我母亲也有一次被抽调到外乡去开挖河流,一去就是几个星期,在回来时还不忘带点好吃的回家,让孩子们解解馋。
有一次,也有一批外乡劳动力来参加我们村附近的开河作业,规定家家户户都得接收入住人员,记得我家也分到二十来位男青年,在客堂内铺上稻草算作他们休息、睡觉的地方。
外乡村民都很客气,他们都是由小队长带队的。当他们见到我家墙上四周都贴满了我画的人物画时,有些好奇,从而开始了交流话题。大家彼此熟悉后,我就用自制的小画板,加上裁好的父亲写废的稿子反面,帮他们画像,一个接一个地写生。因为画得有几分相像,他们都争先恐后地做我模特,我想这时的欢乐确实能化解工友们那疲惫的身体。

我16岁时因在城里借读不顺利,且由于农村户口身份,于是就借着暑假回来准备务农,修地球。村里把我安排到与妇女组一起干些较轻的活,作个过渡。每天按时去田地里与村民一起或碎耕土,或扔秧苗、拍麦。好景不长,还没轮到去做挑担这个重活时,即被母亲撵送到城里重读,以寻找新的机缘。因此,在我人生当中还做过一个月的农民,得到的一点可怜的工分也被划归到母亲那里去了。

后来面临城建,对当地拆迁村民补偿是附近的安置房,多的能有分到三四套,年轻人是最乐意的,他们毕竟也要与时俱进,享受一下现代的城市生活。老人也可以进养老院、护理院照顾,原来的老乡情谊在某种情况下还是会延续,但从此,没有了何家桥。
(作者:老泮,曾用名潘之,美术家、出版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