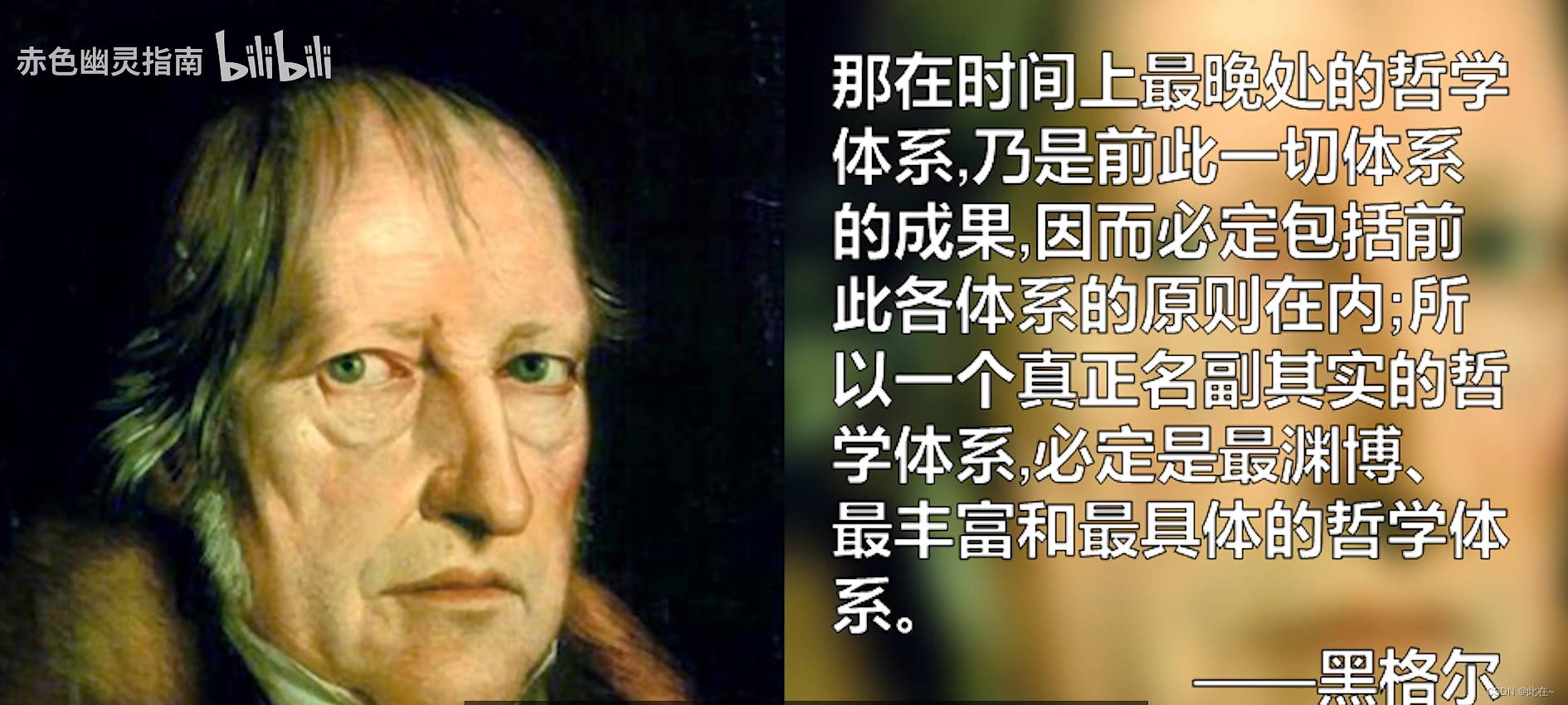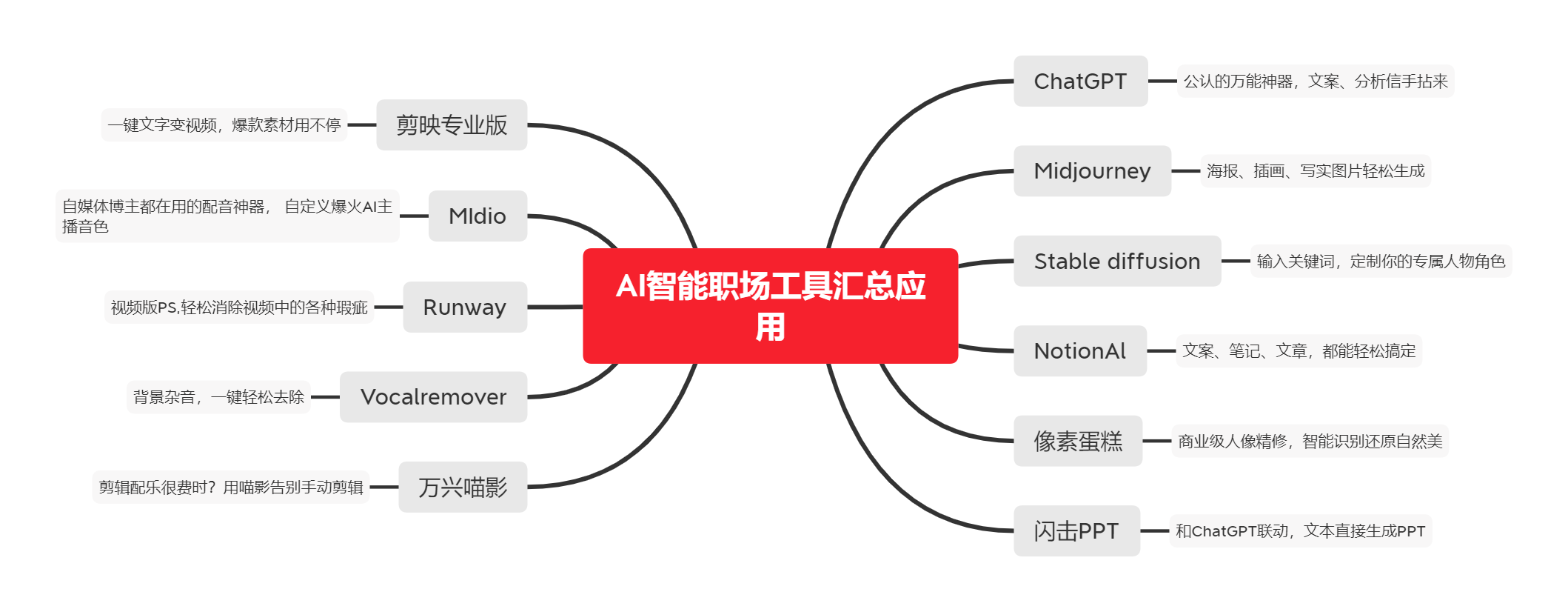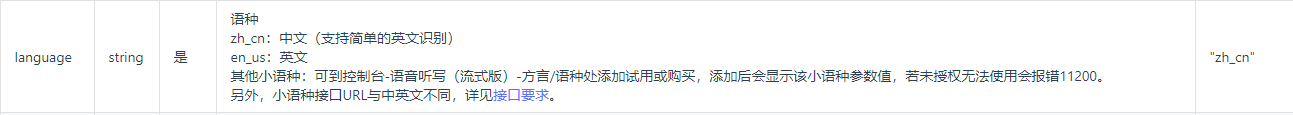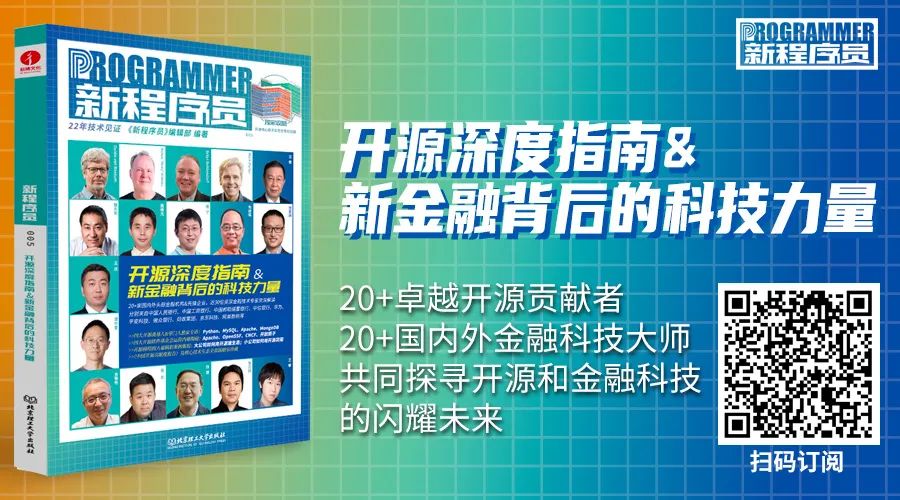有人说:“创新”是西洋画的基调,中国画的焦点是“承传”。就是说,西画必须花样翻新,挑战前人,甚至要推倒重来,唯此才可能在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中国画强调以古人为师,重视师徒之间的陈陈相因。所以,临摹是中国画学习的一个重要阶段,以至很多国画大师都有临摹前人的画稿传世。
但是,“承传”并不是说没有变化和创新,比如自唐、宋以来确立的工笔花鸟画传统,经过元、明、清三代的写意和大写意的变革,尤其是清代宫廷画师,大量借鉴了西方艺术的元素,使中国的花鸟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尤其在笔墨和造型方面有了明显的突破和创新。因此,当代中国的花鸟画家们都背负着沉重的无法超越的传统负累,高山林立,俗套遍布,几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从这个背景和角度来考察刘天怜的绘画,也许更有价值。
刘天怜的创作应该归属中国工笔花鸟画的传统,但是她又是中国传统花鸟画的异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她的作品的构图、色彩、意象、观念等等都与中国传统的花鸟画大相径庭。刘天怜,1987年出生的年轻女画家,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她有扎实的造型训练和娴熟的笔墨功底,但她没有因袭和迷恋传统的路数,而是在遵重传统笔法的基础上,强调了作品的装饰性和构成意义。她试图将勾线、设色、构图,甚至意象等等观念从自身的角色和功用中解脱出来,借助它们之间的关系,点和线、疏与密,静与动、黑与白、圆与三角、具象与抽象等等,在传统与现代的交叉点上,获取一个新的空间和时间的可能性。在她作品的几个最典型的布局中,水管与鱼,方块与鸟,格子与植物,还有那个神秘的盒子。这些带有点线方圆几何意义的构成和似互不搭界的意象组合,让我们产生一种陌生化的美感和惊异。那个连画家自己也无法解释的神秘盒子,在我看来更像是她画面空间之内的另一度空间。从这一点上来看,刘天怜的作品又具有某种超现实主义的预设。当很多年轻的工笔画家在不遗余力地追求超高清写真,试图最大限度地接近所描摹对象的肌理与质地的时候,刘天怜却悄悄地与他们拉开距离,在二维的平面中,利用浓重而又鲜明的色彩、装饰性的叠层平涂,以及几何化的抽象和拼贴,表现了花草、虫鱼、鸟兽在宇宙万物的存在中所处的神奇而又辩证的关联。借用齐泽克的概念,刘天怜的作品所关注的不是我们肉眼所能看到的庸俗化了的“实在界”,而是我们必须用想象与理性创造的“象征界”。它是画家童年愿望的延伸,也是画家对自然与社会秩序的一种概括和思考。视觉给了我们观看现实的本能,却常常遮蔽我们穿透事物表象的能力。西方哲学家(拉康等)利用“凝视”理论,将观看行为赋予了镜像式的互为主体或互为他者的转换,以便让我们更深刻地考察和解释我们所置身的复杂而多元的世界。回到刘天怜的作品,常常让我产生一种错觉,就如同儿时看到的迷宫多维图案,那种精密、繁复的结构,重叠的色彩和交错的映像,要求体验者必须紧紧盯住画面,直到你视觉的焦点慢慢分散、迷蒙,随后突然间转化成一个奇异的多维化的幻境,它让我们震惊的同时,也发现了观看世界的另一种角度和通道。这大概就是我们从童年开始便试图寻找的所谓“奇观”,也是刘天怜作品给我的最直接的感受。
从西方艺术史的角度来反观刘天怜的作品,我不时会发现亨利·卢梭式的稚拙而神秘的空间感,比如她的最新作品《勿听,勿看,勿说》,画面整体由叶子与花朵交织缠绕,人物姿态稚气天真,多种色调的蓝色和绿色营造了一种纵深感,富于节奏韵律的图案和鲜明的色彩,强化了作品中梦一般的童话景观。而古斯塔夫· 克里姆特的绚丽而又奢华的装饰性,在她的绘画语言中也能找到某些根据。这或许与我过于偏爱两位西方大师的作品有关,我无法断定两者对刘天怜创作的实际影响,但是我隐约感到大师的艺术之光无形地投射在她作品之上。
鱼、鸟、鹿、狗、马无疑是刘天怜作品的重要符号。这些符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寓意。吉祥、富足、爱情、忠诚等等。但是刘天怜巧妙地将之转换成了非传统符号,比如金龙鱼、斑点狗、大嘴鸟、长颈鹿,还有非洲的斑马等等,使那些在中国传统花鸟画中早已变得陈词滥调的形态获得了崭新的意象和陌生化的效果。
记得去年在“奇幻世界:刘天怜花鸟作品展”时,有人谈到了花鸟画家如何介入当代社会的问题。她的最新作品《勿听,勿看,勿说》或许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解答。总结刘天怜这几年的创作,我以为,她的画是转入内心的创作。喧嚣的外部现实越来越变得失去了美感,数字化让我们陷入比本雅明所描述的机械复制时代更廉价的现实,所以我们必须找寻或者建立一种新的现实与之对立,这个现实其实就是我们的内心,一个依托想象的空间,这个空间比任何现实更为广阔深远,也更强大,因为它就是雨果所说的心灵的宇宙。
(已发《文艺报》2015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