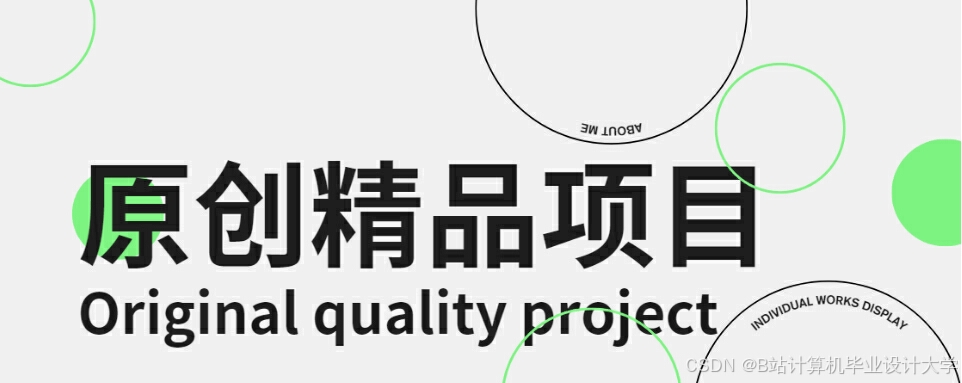专栏简介:本专栏主要面向C++初学者,解释C++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础语言特性,涉及C++标准库的用法,面向对象特性,泛型特性高级用法。通过使用标准库中定义的抽象设施,使你更加适应高级程序设计技术。希望对读者有帮助!


目录
4.6 成员访问运算符
点运算符和箭头运算符都可用于访问成员,其中,点运算符获取类对象的一个成员;箭头运算符与点运算符有关,表达式pt->mem等价于(*ptr).mem:
strtng s1="astring",*p=g&s1;
auto n=s1.size(); //运行string对象s1的size成员
n = (*p).size(); //运行p所指对象的size成员
p->size(); //等价于(*p).size()
因为解引用运算符的优先级低于点运算符,所以执行解引用运算的子表达式两端必须加上括号。如果没加括号,代码的含义就大不相同了:
//运行p的size成员,然后解引用size的结果
*p.size(); //错误:p是一个指针,它没有名为size的成员
这条表达式试图访问对象p的size成员,但是p本身是一个指针且不包含任何成员,所以上述语句无法通过编译。
箭头运算符作用于一个指针类型的运算对象,结果是一个左值。点运算符分成两种情况:如果成员所属的对象是左值,那么结果是左值;反之,如果成员所属的对象是右值,那么结果是右值。